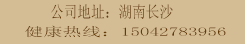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矿山机械设备 > 设备种类 > 嘉兴冶金机械厂启示录
当前位置: 矿山机械设备 > 设备种类 > 嘉兴冶金机械厂启示录

![]() 当前位置: 矿山机械设备 > 设备种类 > 嘉兴冶金机械厂启示录
当前位置: 矿山机械设备 > 设备种类 > 嘉兴冶金机械厂启示录
第一鹰像第16期
文/应丽斋
“冶金厂搬了,老厂房你回去看看不?前两天我姐姐和姐夫都回去看了,他们两个都是冶金厂出来了,那里有他们的青春记忆,以及在社会转型时代洪流里努力跋涉、与命运抗争的足印。那又高又宽的老厂房还在,巨大的航车也在,杂草推里还能找寻到铸钢、铸铁、金工、减速机、动力等老车间的痕迹。有时间的话,回去看看吧!”
昨天,老同事的这个来电,让我的思绪飞奔回到29年前。
当年,大学毕业的我是怀揣着怎样的人生向往,来到冶金厂报到上班的?
当年,还有多少大学生像我一样好不容易跳了农门进了城,还没在计划经济的体制里享受多少荣光,却又不得不迅速直面社会的全面转型,必须在巨变的时代里找寻立足的根基?
当年,这个幼儿园、学校、居委会、招待所、俱乐部、饭店、球场、医院等配套设施一应齐全、拥有多工人、享受县处级待遇的国家二级企业,为什么最终只能走向破产求重生?
当年,企业的运营绩效,又怎样深刻地影响并左右着多工人背后所站立家庭每一位成员的命运?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冶金厂宣传部。因为是职业的缘故,经常要下车间采访,所以,跟当时12个分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很熟。因为亲身经历了冶金厂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每一位个体成员在时代洪流面前那种惶然与不安、那种抗争与拼搏、那种无助与无奈,至今闭上眼还能一一呈现,甚至每每会感慨万千、泪流满面:一个单位的运营好与坏,对员工太重要了!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员工本人,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我虽然在冶金厂呆了只有4年时间,其中一年是产假,但从校门踏上社会后给我上的这一课,太深刻太永生难忘了。
我曾在我人生所出的第一本书——《鹰眼看嘉兴》的前言里这样写自己:“曾经以为一纸文凭、一张城镇户口足以为我的一生构建安耽生活的保证,可刚刚沉浸在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的喜悦中,就经历所入职的国有企业由鼎盛到衰败;曾经以为入职党报当了喉舌可以职业无忧,可不好容易混了点资格,还没来得及享受党报记者的荣耀与尊严,就不得不面对多媒体传播环境下的转型与挑战。这20多年来,总是不停地做梦,梦想自己有一份安稳的、体面的职业,却不曾想命中注定是劳碌的、奔波的。”
是的,命运路上的颠簸,不但让我懂得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工作,更让我明白做人必须居安思危,要始终保持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的拼搏状态。而这样的人生感悟,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工作和生活。每次部门开会,我都会以冶金厂的经历,苦口婆心地对部门的年轻人说:“人生有太多的无常,不能躺在安乐椅上得过且过,一定要增强发展的紧迫感,要把立身的本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父母,不可能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单位,通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荣光,不代表明天就有了保障。”
“我们不能做技能单一的人!我们要多想一想,如果离开当下的平台,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这也是我经常鞭策部门年轻人的一句话。因为,冶金厂破产后,我发现日子最难过、最不知所措的是车间里的那此相对轻闲的人员,其他人都可以迅速在变动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舞台。比如那些搞销售的,他们手里有客户,走上社会后迅速利用自身所积累的闯荡市场经验办起了贸易公司;搞技术研发的,成为民营企业的香饽饽;车间里的技术工人,也凭着手中的技能成了抢手货……只有那些平时坐在办公室发发生产资料、工作相对轻松的工作人员,下岗后就真的赋闲在家。这些人当时能在相对轻松的岗位,其实也需要关系铺垫。可是,当市场的巨浪来临时,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无情。
感谢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社会就给我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我记得,有很多师傅是在年届不惑时,突然发现人生不会按照既定的轨迹走下去,曾经的荣光不再,曾经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职业不再,曾经以为一劳永逸的保障不再……这时候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面对市场毫无竞争力,甚至自身疾病缠身。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有的人的家庭因此而分奔离西,有的孩子因父母下岗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的甚至用死来了却自己的残生。当时还年轻的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实现自身的转型与蜕变。
我听说,当年,上海的宝钢是想把嘉兴冶金机械厂当作它的分厂的。如果没有错失这个机遇,或许冶金色厂可以有更好的结局。
其实,员工是这种结局最痛的承担者。而这样的故事,我所目睹的转型年代里的迭宕命运,经常让我忍不住大声疾呼:作为每一位个体,一定不能安于现状,而是要与时俱进;如果是一名管理者,你的身上背负着员工及其家庭的命运,决策一定不能只求眼前的苟安。失去一个战略发展机会,那很多人的命运会因此而发生变迁。
这就是短短四年冶金厂的经历,带给我的一生的启示!
年,我重新回到破产重组后的嘉兴冶金机械厂采访。此文刊发于年4月27日的《嘉兴日报》上,当时此文还获得了市主要领导的批示表扬。现在再读此文仍然感慨万千。
写在前面的话:
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到嘉兴冶金机械厂采访的。因为嘉冶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里,很多师傅给在嘉兴举目无亲的我许多关爱。
十五年后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采访,看到曾经机声隆隆的厂房如今淹没在荒草丛中,心中充满了感伤。而曾经共事的一名师傅因为患了癌症,因担心巨额的医疗费累及孩子和家人,选择跳楼自杀一事,更让我一连几夜辗转难眠。
如今,嘉冶已不再是当年风光无限的冶金厂,当年意气风发的师傅在岁月的打磨下,多了些沧桑和无奈。但是,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他们依然用笑脸安慰我:“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的达观和自信,还像当年那样令我感动。
嘉兴冶金机械厂凤凰涅槃
对于嘉兴冶金机械厂职工来说,沿袭了数十年的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因为以下两个日子发生彻底改变:
年12月1日,有着66年历史的嘉冶在法院宣告下破产。名员工正式告别国企身份,通过各种形式得到分流安置。
年1月21日,嘉冶原有效资产通过第三次公开拍卖,浙江前程投资有限公司以1.14亿元的价格获得嘉冶的土地、厂房、设备、存货,还有无形资产等。
穿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嘉冶缘何从兴盛走向破产?破产后职工们得到怎样的安置?再就业情况如何?
曾经的贵族没落了———
近10年平均每年亏损.18万元
有人曾用没落的贵族来形容位于市区甪里街号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嘉冶曾经是这座城市时尚的引领者。当我们隔着40多年的时光回望鼎盛时期的嘉冶时,不少职工至今还充满幸福和自豪感。
“我们曾是部属企业,产品遍布全国冶金、矿山、交通、水电、煤炭等10多个行业,部分产品还出口日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由于是重工企业,每月工资也比别人高半级,人家每月领32元,我们有37元。”
“那个辰光,企业福利好得不得了。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是厂里发的,甚至家里用的碗筷、被子都是厂里的劳保。只要市面上一出现新东西,我们嘉冶工人总是率先拥有,厂里办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医院甚至百货商店……就像一个小城市,职工的生活成本极其低廉。”
“那个时候嘉冶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让其他人望尘莫及。大街上只要看到你穿着‘冶金’两个字的工作服,路人就会投来艳羡的目光。男大学生更不用提了,往往一分配进厂,就被家里有待嫁闺女的老太婆们抢去做女婿。”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已成往事。自进入市场经济以来,这家曾有着光荣传统的机修企业,背负着数十年来的体制产物,在艰辛地进行着20世纪的最后一段行程。自年以来,平均每年亏损达.18万元。由浙江万邦会计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年6月30日,企业账面总资产.52万元,总负债.42万元,剔除处理损失.78万元和土地开发费.5万元,实际净资产为负.18万元。企业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由于企业连年亏损,入不敷出,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共拖欠职工医药费万元,拖欠电费万元。
大伤元气———
一座5吨电炉套牢一个厂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拥有同样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每个破产企业的背后,都有必然和偶然因素,有值得后人借鉴的教训。
在有着36年工龄的王师傅眼里,嘉冶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最大的遗憾是错失与宝钢合作的机遇。他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海宝钢相中嘉兴冶金机械厂在国内一流的机修能力,曾想方设法让嘉冶成为集团公司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嘉冶没有答应。
“后来,宝钢把苏州冶金机械厂和常州冶金机械厂纳入麾下,并且双方合作由最初的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本来境况远不如嘉冶的苏冶和常冶在宝钢这个强有力的靠山支持下,获得了迅猛发展。”
20年后的今天再回首那次不可多得的机遇,职工们无不扼腕叹息。领导企业就好比驾驶员开车,手中的方向盘稍一偏,车辆就有可能进入另一条车道,带给职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不过,真正让嘉冶元气大伤的是‘八五’期间举全厂之力改建的铸钢车间,特别是年上马的5吨电炉技改项目。
这幢冶金厂最新的建筑,如今四周已枯草蔓延、锈钢横陈,荒废多年。
职工说,当时,钢锭成了市场抢手货,根据报表,全厂多万元利润中,有90%来自钢锭。为了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厂方决定以高于银行利率15%的利息,向全厂职工集资再建一座5吨电炉,扩大钢锭生产能力。
一时间,5吨电炉成为全厂名员工的寄托。然而,5吨电炉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第二年,钢锭的市场行情一跌再跌,每名职工集资元的技改项目没有产生一分效益就被深深地“套牢”了。
“技改要有前瞻的眼光,不能有从众效应,否则永远落伍别人半拍赚不到钱。”这是5吨电炉留给冶金职工的切肤之痛。
体制之痛——
1名在岗职工需负担1.6名离退休人员
机遇的错失和技改的失败,让企业的经营环境与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而影响和阻碍企业生命活力的真正障碍是,传统体制下积累的弊端已使嘉冶难以面对市场经济的法则。
近10年,嘉冶也屡屡挥动改革的刀刃,寻求扭亏为盈的解困之路。在年、年和年3年间,嘉冶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内部下岗分流富余人员工作,近名员工提前内退和下岗在家。
“原以为把富余人员打发回家,本来由三个人做的活交给两个人或一个人做,企业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反而加重了企业负担。”原嘉冶的法人代表曹耐峰告诉记者,到企业破产前,冶金厂有各类人员人,其中在岗人,离岗退养人员还有人,离退休人员人。离岗人员按人均每年元计算,富余人员每年仅人头费一项就增加企业成本多万元。此外,离退休人员给企业增加的负担也很重,差不多1名在岗职工需负担1.6名离退休人员,对这部分人员每年需支付养老保险统筹费、医药费等各项支出在万元以上。
曹说,如果没有这万元的历史负担,冶金厂每年可实现盈利万元,职工们完全能自己养活自己。
严酷的现实让职工们开始逐渐明白,如果不从体制之内进行根本性改革,历史的负担难以消除,再怎么努力,企业的困惑和困境依然会持续下去。
冶金厂被划归浙江冶金集团管理后,为了实现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三年两目标”,早在年3月和年8月,杭钢会同浙江省冶金行业管理办公室,派出了改制工作指导组驻厂调研指导,并拟定和上报了“分兵突围”的“改制脱困总体方案”,让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组成若干个经济实体,率先冲出亏损重围,但内部的改良终难革除国企留下的种种弊端,最终,这个方案只持续了天。
从年9月省级领导确定破产方向开始,嘉冶上上下下开始了望眼欲穿的守望,谁也不曾想到,从确定企业破产到正式付诸实施,整整历经5年时间。
这5年,冶金厂日子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面对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破产的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提货商都无情地掐断了资金链,供应商对嘉冶发出了“钱不到就不发原料”的指令,订货厂家则打着“货不到就不付款”的旗号,银行也关上了信贷大门。
虽然四面楚歌,但嘉冶领导和员工们仍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维持正常生产。
这些年来,但凡自己有点技能、家里有一点门路的人都跳槽了。留守的职工大多是因为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无法在外面找工作的。
冶金厂的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到破产前,冶金厂在职职工平均年龄49岁,平均工龄29年,30岁以下的只有32人,企业已连续5年没有招过员工。
浴火重生——
0多职工平稳分流
许多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都伴随着剧烈对抗与震荡,但嘉冶的员工们平静地接受了现实。
“嘉冶破产重组能够圆满完成,既有员工心理承受能力增强的因素,更离不开过实、过细的工作。”市国资委一名工作人员说。
员工们坦陈:“搁在10年前,听说企业破产也许会茫然不知所措。这10年看得多听得多了,心里承受能力变强了。”职工们明白,国企改革是一种痛,更是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机遇。
其实,到目前为止,嘉兴所有企业的破产还没有哪一家像嘉冶一样受到那么多省领导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kuangshanjixiea.com/sbzl/14005.html